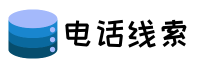无可否认,一些迹象表明对“法院程序”概念的解释过于宽泛。因此,《联合国法院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将“法院”定义为“一国任何机关,不论其名称如何,有权行使司法职能”。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评注则对“司法职能”作出了广义的定义,并承认该定义“在不同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下,可能涵盖国家特定行政机关行使命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有时被称为‘准司法职能’”)。
然而,。显然,此类制裁的实施与“诉讼
或争端解决的裁决”或“法律和事实 巴西数据 问题的裁定”无关。它也不是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评注所定义的“通常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或在其管辖下行使”的职能。相反,它主要属于行政部门,也可能是立法部门的事务,并且完全属于实施制裁国家的外交政策范畴。即使制裁针对的个人或实体可能决定通过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启动法院程序来质疑制裁的合法性(例如,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撤销诉讼),但这并不能改变制裁本身通常并非源于任何“法院程序”的事实,也不会将其追溯转化为“判决前”的约束措施。用朗齐蒂的话来说,资产冻结是“立法或行政部门自主决定的措施”,而非“判决的延续”的强制措施。因此,初步结论是,针对一国及其机构的金融制裁不会触发国家豁免制度,因此不会导致违反国家豁免规则。
如果国家豁免规则不受影响,那么“不可侵犯性”又如何呢?国际法确实区分了豁免和不可侵犯性——尽管两者之间 从任何位置执行和控制服务以及安排报告 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一些条约文书规定了第三国拥有(或有时使用)的特定类型财产某种形式的不可侵犯性。明显的例子包括外交使团的财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2条)或“特别使团”的财产(《特别使团公约》第25条)。另一方面,目前尚无涵盖所有国家财产的类似公约制度,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种保护是否仍可在习惯国际法中找到。在上述澳大利亚与东帝汶之间的国际法院程序中,两国对这个问 邮寄线索 题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答案。
然而,沃茨和詹宁斯在
年版的奥本海姆国际法著作中似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国际法似乎并没有任何普遍要求,要求所有此类财产仅仅因为属于国有,就应享有任何特殊的不可侵犯性或其他豁免权,免受其所在国政府行为的影响”(第111段)。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近期制裁实践似乎支持后一种观点(有趣的是,一些认为金融制裁违反豁免规则的作者至少承认,习惯国际法的演变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例如,参见卡斯特拉林)。